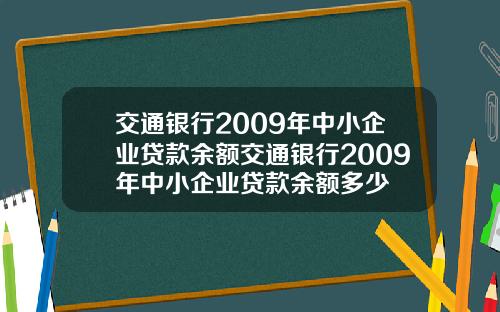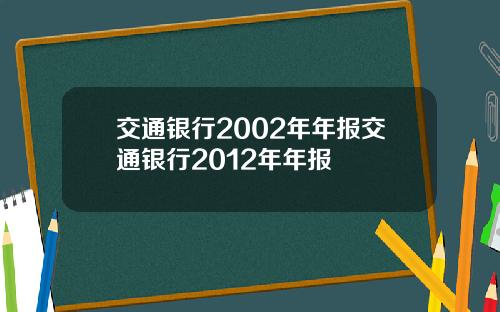化冶所,一个亲切的名字
化冶所,一个亲切的名字
陈九
一九七六年我从铁道兵复员后就在化冶所做实验工。化冶所全称是“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”,现在改名叫“过程工程研究所”。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工作单位,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,与国相息,倍受滋养。
开始分到化冶所是说盖房子,进去才知道不那么简单。都说中国是个缺乏铁矿的国家,但情况比这要复杂。我们缺的是铁含量高的富矿,却拥有大量复合共生矿,即以铁元素为主,同时含钛锰钨镍等稀有金属,混在一起难解难分。比如四川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就是典型一例。对这种铁矿,用传统高炉冶炼损失太大,稀有金属都烧光了,那也是国家急需的金属原料。化冶所的使命就是研究用化工的方法炼铁,同时提取稀有元素,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冶金之路。我参与的第一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就是“流态化炼铁”的中间试验,代号“四零车间”。该项目由化冶所所长郭慕荪院士主持,他曾在西德和巴西考察研究,回国后提出动议并经国务院批准,兴建我国第一个流态化炼铁试验基地,这正是我们要盖的“房子”。
所谓“流态化炼铁”是用化工方法提取铁元素。基本步骤是,先把复合共生矿磨成细粉投进反应釜内,通过输入氧化和还原气体进行化学反应,最终在不同反应时间和反应位置,获得纯铁粉和其他稀有元素,最后将铁粉压块后直接送电炉炼钢,我们建就是流态化反应釜及配套设施。
当年“四零车间”的条件非常简陋,四个复员兵,加上科技学校分来的十几名中专生,我们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,脚上一双“踢死牛”的翻毛皮靴,开始了繁重的劳动。从清除工地上各种遗留物,挖地基,在清华园火车站卸砖卸水泥,再到盘钢筋浇灌混凝土,基本全靠人力。科研是烧脑的高贵的,但转化为应用过程却是艰苦平凡的,我现在明白为何改叫“过程工程研究所”了,因为研究对象扩展了,反应过程中的理论和工艺方法既可以是化工的,比如流态化炼铁,也可以是物理化学混合的,甚至可能是生物的,将反应过程工程化应用化,变成生产工具,所以它命中注定是高贵与平凡的组合。
说到高贵与平凡我有点情不自禁,那时对该命题的理解很简单,就是才华加献身精神,不不,不光献身精神,还有献身的行动。比如郭慕荪院士,他经常在四零车间粗糙的地面上徘徊。试验的结果并不理想,矿粉打结,反应不充分,气流不均匀,反应釜内有死角,用何种催化剂来改善反应效率,都困扰着这位留美归国年逾六旬的著名科学家。
那天我在清理散落的铁粉,纯铁粉的颜色是黑蓝色的,只听有人叫我,小陈快过来帮帮忙!我抬头一看,只见郭慕荪先生站在流态化床的一处开口,他显然试图爬进去,浑身上下已被铁粉染成黑色,脸上都是。郭先生您要干嘛?我要进去。里面那么脏您进去干嘛?我要看看打结的情况,你推我一把快点快点。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,把郭先生推进流态化床。这时四零车间负责人李茂林看到我,小陈你干啥呢,身上黑乎乎的?我说我刚把郭先生推进流态化床里。哪个郭先生?郭所长郭先生啊。什么,赶紧进去看看他咋样了?我和郭先生出来时全身都黑透了,那是我平生最黑的一天,我用最黑的平凡匹配郭先生最黑的高贵,李茂林说,郭先生这种事干多了,在西德巴西都干过。
流态化中间试验应该是成功的,每天获三吨铁粉,还有其他稀有元素,在理论走向实践上迈出一大步,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。遗憾的是,当继续扩大实验时却遭遇瓶颈,同样的工艺,按比例扩大结果却完全不同,无法形成生产规模,只得稳住脚从长计议。我们这些年轻人也陆续被分到各个科室,以实验工的身份参与其他项目。我去的是陈家镛院士领导的第四研究室,参加等离子喷镀项目的实验工作。所谓等离子喷镀是利用等离子弧的高温流动气体,将稀有金属元素的粉末喷镀到某种基体上,以改善表面性质。该项目针对的是小浪底水电站水轮机叶片的腐蚀问题,被腐蚀的叶片导致发电率极大降低,这在当时是迫在眉睫的难题。
等离子喷镀工艺今天已常规化,当时却是零突破。我参与的部分是实验生产喷镀用的镍包铝和镍包石墨粉末,白手起家积累经验和数据,彻底摆脱依赖国外昂贵的同类产品,这是该项目的关键。在科室指导下,具体操盘实验的却是一位姓黄的退伍老兵,湖北汉阳人,性情豪爽。他说小陈,老子也是复员兵,当年炮八师的瞄准手,老子干得来,你一定干得更好!实验过程中,镍包石墨的形成总不够充分,粉末切片在显微镜下显示,外边的镍往往只包住一半,难以闭环,这样喷到基体上涂层不均匀,无法达到每平方厘米三公斤的亲和力,怎么办?科学家对此一筹莫展,他们只知道镍包石墨是完美的元素组合,既抗腐蚀又提高表面光滑度,至于如何让镍不薄不厚,完整包住石墨颗粒,最好还是去问老黄。高贵与平凡在这个节点上再次平起平坐,缺一不可。
老黄真不含糊。他说小陈你就负责记录,一切数据,压力温度时间,注入液体镍的时刻,液体镍的温度,石墨颗粒的细度,等等等等,都给老子记下来记清楚了,一点不能差,老子就不信了,一江山老子都打下来了,还搞不定这么个事。我们那时真是夜以继日,什么上班下班周末周日,吃完东西就来,睡醒觉又来,反复实验反复调整,比如石墨的细度,是二百一十目还是二百二十目,要不要先洗一下,用什么洗,采用何种洗涤剂,这里有无限的组合和选择,靠我们无数次实验,从无数次实验中产生的灵感,摸索着最佳数据和具体步骤。庆幸的是,在这个项目上我们是幸运的,小浪底是幸运的,我们最终生产出完美的喷镀粉末,填补了空白,并总结出一套转化为生产规模的工艺数据,移交给相关厂家。
后来在漫长的漂泊中,每当看到小浪底水电站的消息,泄洪啊冲沙呀,我都会停下来,凝望远方很久。我把一部分青春留在小浪底,留在了那条叫黄河的激流之中,这是我最大的满足。我养过一只叫“小白”的猫,后来丢了。多年后在离家很远之处发现了她,我觉得她很像小白,便大喊一声“小白”!没想到她立刻驻足看着我,跑到我的身边,我就是小浪底的小白。还有我的师傅老黄,网上流传过一首叫《汉阳门花园》的歌,“小时候民主路没得那多人,外地人为了看大桥,才来到了汉阳门,……冬天腊梅花,夏天石榴花,晴天都是人,雨天都是伢”。我哼唱这首歌时会热泪盈眶,老黄撸胳膊卷袖子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,他是汉阳人。历史很少为平凡举杯,如果遇到他,何不让我们同醉。
随后我转入蔡志鹏先生领导的第一研究室,从事湿法冶金的实验工作。与此同时,国家咣啷一下恢复了停置已久的高考制度,给我的生活带来震荡。我心中早有大学梦,哪个年轻人不想进步,做个独挡一面充满创意的专业人士?但当时上大学全靠选派,名额极少,我根本不敢想,心说咱都参加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了,在实践中学习未尝不可,总比混日子强吧。可现在怎么办,人家真公开招生了,期限紧迫,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,总不能装糊涂吧?
做实验时我开始走神,睡不着觉,还经常发呆,掉头发也从那时开始,原来头发又浓又卷,波浪大弯,打那起一天天不灵了。有一回我在公交车站被邻居阿姨拽住,孩子,叫你半天为啥不理人?中邪了你,要不要去看看?我如梦突醒强撑着跟她开玩笑,去哪看呢阿姨?去哪,还能去哪,安,安,安定医院呗。说完我俩都大笑起来,安定医院是精神病院。当时我就是特心虚,咱连初中都没毕业,虽然私下也在补习,来得及吗?化冶所不少年轻人都跃跃欲试,人家要么读过高中要么老三届,功底扎实,看着他们我太自卑了。那天蔡志鹏先生,我们都叫他老蔡,他是东北人,做过鞍钢的副总工程师,直截了当问我,人家都准备高考呢,你咋想的小陈?我底子太薄,够呛。啥意思,你不准备参加了?嗯,差不多吧。老蔡愣住了,缓半天说了句让我绝地而起的话:我真把你看走眼了小陈,原来你是这么个人,啥都别说了,干活吧,把那些试管洗出来。
等等,我不是“这么个人”。
根据老蔡安排,只要完成实验准备工作,我就可以去图书馆复习。当时化冶所的气氛是,对复习的年轻人会多一声问候,小陈啊,又复习那,你准备考什么科呀?文科。文科好,你像文科的料。所办主任靖冠英,一个抗战老兵,在会上公开表示,各科室要支持年轻人考大学,在做好本职工作前提上,尽量给他们留复习时间。最生动的当属郭慕荪院士的夫人桂老师,她也是留美硕士,还是化冶所图书馆馆长,她只要在楼道里看到我们就往图书馆轰,拍我们的肩膀像赶羊一样,快点快点,抓紧时间,你们落课太多了。她还开班为我们补习英语,可惜我连二十六个字母都念不全,不敢上她的课。我当时最常用的是图书馆二楼东头那张桌子,宽大明亮,透过窗户能看到对面三星铅笔厂的车间,当年著名民族品牌“中华铅笔”就是他们生产的。我看到那些匆忙的身影和机器的节奏,赶紧埋头温书。
七七年没考上,时间太仓促了,我们多半考生都没考上。这就产生一种蝴蝶效应,人多势众,没考上接着考,所里的氛围依旧是包容的。我发现我的问题出在数学上,人家是复习,我是现学,而且考题逐年加深,不突击根本追不上。那天我对老蔡说,能不能让我最后一个月拼一下,把数学整上去?他说不行,所里没这规定。可第二天上班,我刚进屋老蔡就叫起来,小陈你脸怎么是绿色的,别考不上大学再出人命我可负不起责任,赶紧回家休息,休息好再回来上班。
湿法冶金的实验工作我做的很有限,都忙复习了,无法像“流态化炼铁”和“等离子喷镀”那样说得头头是道,前两项我毕竟全身心投入,闭上眼都能说出实验过程和化工反应中的常见问题。特别是镍包石墨生产工艺,我甚至能写一本工艺手册,把最敏感的步骤列出来供人参考。可在最支持我的人主持的科研项目上贡献最少,我没为蔡志鹏先生做过什么,这一直让我羞愧。有时我问自己,当年留下来搞科研会不会更好,还有什么能让我更满足呢?
七八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,离开了化冶所。正值金秋,斜阳把我的身影像思念一样拖得很长。他们送我到大门口,有长者,同事,还有心爱的人。虽然短短两年,我从初中生变成大学生,这对青春而言足以刻骨铭心。但更难忘的是参与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,感受到高贵与平凡的奉献精神,这才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发动机。特别是今天,科研创新已成为存亡之关键,过去全部科技积累,此时都堪称是逢凶化吉的杀手锏。化冶所依然前行,改名为过程工程研究所后研究范围更广泛更深入,这都让我倍感欣慰,一往情深。
那天我情不自禁找到化冶所旧址,重新走进那个院子,那座楼,图书馆,和我工作过的实验室。我看到当年的同事和年轻的自己,波浪大弯,在我身边走来走去,像真的一样对我微笑。
2022年1月22日京东大望路
原载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2022年5月2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