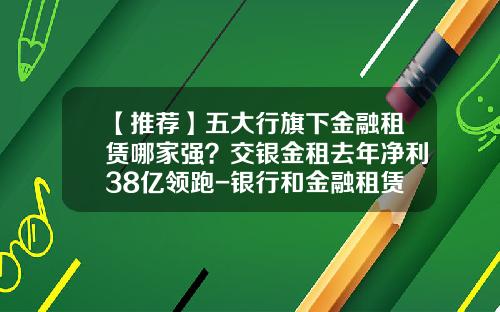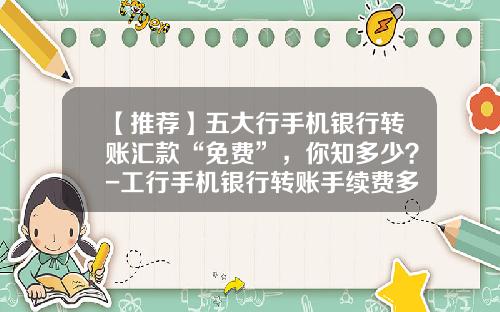一个写入生命的名字
转眼,父亲节又至,而我却再也没有了父亲。
三年多以前,父亲在他68岁生日刚过没几天,怀着对美好生活无限的留恋,怀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冀,静静地走了。留给我们的是他曾参与建设过的那无言的世纪丰碑,是勤俭节约、吃苦耐劳、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。
兵娃子
父亲出生于解放初期,名叫喻祖兵,之所以取这个名字,是因为爷爷奶奶感恩于共产党解放军将他们从水火中拯救出来,希望父亲以后当兵保卫祖国。
父亲18岁时,奶奶响应国家号召,将正值青葱年少的父亲送入了部队,奶奶希望父亲在部队好好磨炼,学本事,增本领,有机会保家卫国。父亲佩戴着大红花,身穿绿色军装,告别亲人,坐汽车、乘轮船,辗转几天几夜,历经长途跋涉,到达了心中向往的绿色军营,成为了一名真正的“兵娃子”。
父亲很是珍惜部队学习锻炼的机会,作为通信兵,他熟练掌握使用各种通信设备,业余时间,他学习写字,自学文化课,其中居然还包括英语。难以想象,小学没有毕业的父亲,却自学了英语,后来还成为了我的英语启蒙老师。
父亲写得一手好字,飘逸洒脱的那种,他一向以此为傲,我也从小就经常模仿父亲的字体,所以我写的字似乎带有父亲字体的风格。
父亲说,部队是个大熔炉,在那里,他不仅学习了军事技能,学习了文化知识,更重要的是,他深深体会到报效国家、献身使命是具体的,只有立足本职,练就过硬本领,才能更好地履行使命、不辱使命。就是因为怀揣报国梦想,服役期间,父亲苦练本领,钻研业务,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。
船拐子
1971年,父亲三年服役期满转业。那时正值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。
随着工程开工,十几万建设大军,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宜昌。父亲服从组织安排,也成为了葛洲坝建设大军的一员。父亲说,他生在和平年代,当兵时没有打过仗,但能参与到葛洲坝工程的建设,也算是为国家贡献了力量。
考虑到父亲在部队对机械设备有一些了解,他被分到葛洲坝路桥公司的前身三三〇指挥部砂石分局,成为了752采砂船的一名轮机操作手,主要负责从河下开采砂石供葛洲坝工程建设使用。父亲曾自我调侃地说,他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葛洲坝的“船拐子”。
我小的时候随父亲在这条船舶上玩过,船几乎都是停在江中心,只有检修的时候才会靠岸。
这艘船船体很大,共四层,第一层主要是船舶发动机等,第二层是可容纳几十人的餐厅,还有厨房,里面弥漫着米饭的香味,这也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,既可以闻饭香,又可以在餐厅看电视。
第三层是船员房间,估计有二十多间,空间很小,里面有一张高低单人床,一张写字桌,其余基本没有多余的空间了,窗户是圆形的,就如坦克的开闭窗。
第四层便是操作台,有好几十个各种颜色的按钮,曾看过父亲操作,倍感神奇。随着父亲按下按钮,船体外的砂驳一会儿进入江底,一会儿满载砂子出水运送到旁边等候的运输船。可是在感觉神奇的同时,也因噪音太大而难以忍受。可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了近二十年。
曾问父亲干嘛不换个工作,在船上,工作环境既单调枯燥,噪音又大。父亲说:“工作总得有人干。再说了,我的工作环境算是很好的了,住在船上,生活设施齐全,好多葛洲坝人住的是芦席棚,或干打垒。相比之下,我算是很幸福的了。”
我们举家从老家搬到宜昌,住了好几年的芦席棚,就是那种墙体由红砖砌成,屋顶盖的牛毛毡,夏天似蒸笼,冬天勉强避寒风。芦席棚是当时葛洲坝建设者施工期间曾住过的工棚。
后来,随着城区改造,那些有着深深历史烙印的芦席棚便成为了葛洲坝人永远的回忆,而我的父母也搬至公司建的经济适用房。
父亲一辈子话少,很少讲起他工作上的事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,与父亲聊到了葛洲坝大坝合龙的情景。父亲说,葛洲坝工程建设时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便是在每秒4720立方米流量的长江上进行大江截流。截流能否成功,直接关系到整个葛洲坝工程的成败。
父亲所在的752船也承担了合龙的任务。在合龙前,也就是1980年底,单位进行了总动员,职工分成几批,党员冲锋在前,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。第一批牺牲了,第二批上……
说及此,父亲笑了笑说,还好最坏的情形没有出现。原计划7天完成截流,结果只用36小时就完成了。
1981年1月4日19时53分,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,实现了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。
父亲说,当时我妹妹出生才五天,他没有在旁照料我母亲,这事挺对不住我母亲的。说及此,父亲仰起了头,我分明是看到了他眼里的泪花。父亲用几句话似乎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了当时合龙的情形,可那惊心动魄的过程,只有老一辈葛洲坝建设者方才知晓。
砂石佬
1988年12月,随着最后一台机组投产,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全部建成,葛洲坝集团也开始由指令性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,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全面抢占水利水电工程市场。
作为“船拐子”的父亲也告别了工作近二十年的752船,奔赴清江隔河岩水电站,从一名船舶轮机工成为了一名主要从事碎石筛分运输的皮带工,成为了一名“砂石佬”。
当时完全使用的是传统的生产技术,砂石破碎时的灰尘满天飞、声音震天响,蜿蜒几十米的皮带机整个裸露在外面,每隔一段就会需要一名工人守着,谨防皮带断裂等安全事故发生。
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,两个人面对面说话也只能靠吼,要不然听不清。工作一天下来,工人从头到脚落满了灰尘,完全成了一个“灰人”。据此可以想象父亲当时的工作环境。
后来,我给退休在家的父亲讲起现在砂石生产工艺,父亲没有为当初工作环境艰苦而抱怨,而是为公司的发展而感到开心。他说时代在变化,公司在发展,你们赶上了好时代,要好好工作,最起码对得起公司给你们发的工资。
没有豪言壮语,父亲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了一名老党员、一名普通职工的强烈责任心和对企业的深深情怀。
1995年,随着三峡工程开工建设,父亲又根据公司安排,奔赴到三峡古树岭碎石加工系统。
古树岭人工碎石加工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碎石加工系统,每天源源不断地为大坝输送着骨料,是整个三峡大坝的主要“粮仓”之一。
作为带班班长,父亲很少请假回家,不顾震耳欲聋的碎石噪音、呛人难受的粉尘,每天与工友一道坚守现场,跟踪监测设备运转,查看砂石破碎筛分情况,为的就是确保大坝砼浇筑的顺利进行。
为此,我母亲也会有抱怨,说父亲对家里三个孩子不管不问,只顾着工作。
说他只不过一个普通工人,需要那么拼命吗?不善言语的父亲没有与我妈做过多的争辩,只是说,虽无官无职,但凭一份责任心,尽力把事情做好,让母亲多理解。
母亲本是通情达理之人,小小的抱怨也只是不想让父亲那么辛苦。对于执拗的父亲,母亲终究没再说什么,只是叮嘱父亲注意休息,保重身体。但父亲依然如故,一直忙碌在三峡建设的一线。
1997年11月8日8时30分,随着3发信号弹腾空而起,在上、下游龙口的4个堤头整装待命的400余辆自卸斗车长龙般开始轮番发起背向江流的抛填……15时30分,上游围堰的戗堤合龙,大江截流首先在上游龙口一举成功。
18时30分,下游围堰戗堤在暮色中又胜利合龙。大江截流至此圆满成功。
守在公司项目部电视机前的我,努力在现场欢呼的人群中寻找父亲的身影。
那个时刻,我是开心的,我是自豪的,因为这即将建成的世纪丰碑中凝结着我父亲的汗水与付出。
路桥人
三峡完工,水电市场也在逐步萎缩。由于公司任务不饱满,一些职工在家待岗,父亲也成为了一名待岗人员。
劳碌了一辈子的父亲在此期间也没有闲着,他收过废品,也卖过小菜,经常凌晨两点到大公桥进菜拖到西坝菜场卖。然而并没有赚到什么钱,赚的也只是卖剩的菜。
母亲曾笑父亲虽然跑得欢,钱却没赚到,还不如在家呆着,说我参加工作了,她做裁缝也能赚些钱,一家人节约着也能过。
乐观的父亲却自嘲地说,他主要是为了了解民情,不在于赚多少钱。他说他相信公司的困难是暂时的,过不了多久,他便又会重新上岗。
正如父亲所预料的,他在家待岗时间并不长,1998年,公司从水电领域转战路桥领域,并成功中标了公司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——贵新高速公路,并以贵新高速为发端,先后中标砚平、元磨、山西祁临等高速公路项目。于是父亲又转战高速,成为了一名路桥人,直至退休。
母亲曾说父亲是个全才,懂机器,开过船,做过皮带工,还能修路。父亲说,这都是单位给的平台,单位转型,职工不跟着进步,如何跟得上公司发展步伐。
父亲退休在家后,在含饴弄孙的同时,仍关注着公司的每一点变化。每每讲起公司的发展,父亲的喜悦之情便溢于言表。
天不佑人。2017年9月底,当一家人正筹备着准备回老家过国庆时,一向康健的父亲,却突患重疾,于我们就如天塌一般。可乐观的父亲却反过来劝我们。
父亲病重时,还常常念叨想回宜昌,想看看葛洲坝,想上三峡坛子岭。可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在恶化,到2018年8月初,走路已是很勉强,意识已不太清晰,医生让我们做好最坏的准备。
母亲说:“叶落要归根,送你爸回老家吧。”听从母亲的安排,我们将病重的父亲送回老家。回到老家县城,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出了火车站,我问父亲:“爸,你知道这是哪里吗?”声音早已嘶哑的父亲用很微弱的声音说:“葛洲坝。”
泪水瞬间涌出了我的双眼,我的父亲啊,您一辈子奋战在葛洲坝,在您生命最后的时刻,您心里想的还是葛洲坝啊……(喻碧)
来源: 光明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