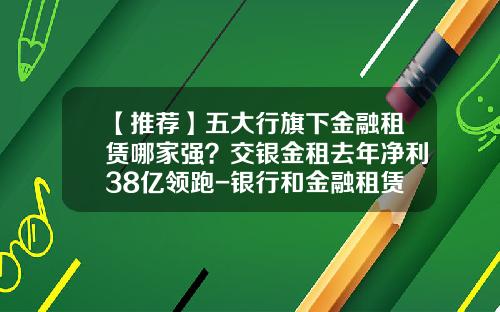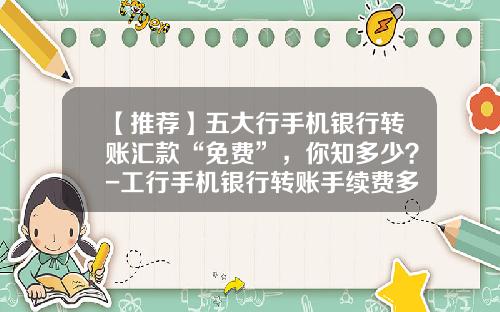【高手在民间】三代当炉
1
馍·干馍·干馍馍
李文虎,可能是中国最不赚钱的手艺人。
8月25日,李文虎两口子起了个大早,不到7点就来到打干馍馍的出租屋。和面、擦酥、揉捏、捣碾、上炉。8点半,第一鏊8个干馍馍出炉。
平时,李文虎上午9点前开工,上、下午各打11斤白面的总计百十个干馍馍。这天开工早,是因为头天晚上一位老主顾打电话,说次日上午要早些过来买15个干馍馍回村看亲戚——当日打下的黄昏时分已售罄,只得次日早早动手。
翻烤
李文虎打的干馍馍,向来是随打随售。顾客登门购买,概不外出摆摊。一鏊8个干馍馍,揉捏锤敲、正反烘烤各需半小时。二两生面打一个,每个售价两元。李文虎忙碌两小时打出两鏊,当天第一笔生意得款30元——这只是毛收入,刨去面粉、胡油、燃气的成本,纯利润不过15元。一天打百十个,挣个百把块。
接过焦香缭绕、尚有余温的干馍馍,老主顾如释重负,连连道谢。说,村里的姑姑早就惦记着这一口了。忻州的干馍馍,她家老辈儿只认这李家的。李文虎摆摆手:“那是老人吃惯了。老人今年多大岁数?不敢定小时候还吃过俺爷爷打的干馍馍咧……”
干馍馍是老忻州的特产——忻州独有,外地皆无。这里说的老忻州,指过去的忻县、现在的忻府区。忻州市其他特色食品,比方蒸肉,忻府区有,定襄县也有;比方碗饦儿,保德人会做,偏关人也会做。其加工制作方法一般无二,不好说谁的更正宗、更地道。惟独这干馍馍,只在老忻州才有。
蒸肉 碗饦
馍,干馍,干馍馍,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馍,北方人多叫馒头。《三国演义》中,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蛮后班师路过泸水,风浪大作无法渡过。孟获献策:此乃河神作祟,须用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。诸葛丞相何等仁慈,岂能滥杀无辜?“遂命行厨宰牛马和面为剂塑成假人头,眉目皆具,内以牛羊肉代之,为言‘馒头’奠泸水,岸上孔明祭之。祭罢,云收雾卷,波浪平息,军获渡焉。”“馒”音通“蛮”,“馒头”意为“蛮头”,民间传说这就是馒头的起源。
最早的馒头“内以牛羊肉代之”,这岂不就是肉馅?这样的“馒头”岂不就是“包子”?到了宋代,包馅的“包子”一词才发明出来,不过此时馒头又被称作“炊饼”——就是武大郎挑着担沿街叫卖的那种。据说到了清代,“馒头”和“包子”才彻底区分开来。如果严谨地定义一下,馒头,就是一种“把面粉加酵母(肥头)、水、食用碱等混合均匀,通过揉制、饧发后蒸熟而成的食品。”包子,就是“用发面皮包馅蒸成的食品。”不过,如今上海、江浙一带,仍有人把包馅子的叫作“馒头”,比如当地特色美食“生煎馒头”“蟹粉馒头”,其实就是生煎包子、蟹粉包子。
干馍,陕甘宁青一带又叫锅盔。用鏊烙制,面饼直径二尺开外,又圆又厚像大铁锅的锅盖——所谓“陕西十大怪”:面条像裤带,锅盔像锅盖……不过,这里说的“干馍”或者“锅盔”,又同忻州人常见的“原平锅盔”大异其趣。“原平锅魁”面饼呈黄色,长方块形状,有不包馅的空心锅魁,也有甜馅锅盔。据说当年慈禧“西狩”路过崞阳,当地官员献上“锅盔”。西太后没有见过此物,说“原平锅盔”长得像“鞋底儿”。至于把馍头切片烤干,叫干馍也行,叫干馍片更准确。
原平锅魁
干馍的“馍”字一叠音,“干馍馍”就成为与干馍大相径庭的另外一种食品。不用发面,揉捏、锤打成特殊的造型:正反两面中间凹进,烘烤时圈状凸起部位接触鏊底,烘烤后凹进部分膨起。因为出炉后正反两面都有焦黄的圈状凸起,看上去像两层楼,老忻州人也把它叫作“干楼儿”。
“李家干馍馍”
干馍馍不算主食,没有谁家说今天午饭吃了干馍馍。但它也不是零食,谁的口袋里也不会装个干馍馍。在老忻州人看来,干馍馍就是用来“搬着”吃的——饭点未到肚已饥,吃半个干馍馍;食欲不振不想吃主食,来一个干馍馍。过去,干馍馍的服务对象似乎更偏重于老头、老太。牙口不好了,偏要掰一块比较坚硬的干馍馍,含在嘴里待其慢慢洇濡发软,吃进肚里反而更易消化。现在,忻州所有打干馍馍的师傅中,只有李文虎一人用老辈儿留下的炉鏊烘焙,只有他按其家传的手法“擦酥”,因此李家的干馍馍除了“干”,还兼有酥、绵、脆的特色。
李文虎世代居住忻府区西街村。祖父李有年将打干馍馍的手艺传给其父李黄根,父亲又传给他,是谓“三世当炉”。李文虎从1996年放下木匠营生重操祖业,至今也快30年。
2
“老忻州”的乡愁
每个地方的特色食品,与这个地方的物产密切相关,体现在当地的地理气候、人文历史和生活习惯等多个方面。物产丰饶,特色食品自然丰富多彩;物产单调,特色食品难免乏善可陈。
忻州豆腐脑。图片源自“忻州记忆”
三四十年前,外地人调侃忻州(忻县)人:你们忻州有甚了?除了“茭的鱼儿”,就是“豆腐脑儿”,此言倒也不差。历史上,忻定盆地盛产高粱,百姓只能把高粱面的做法推敲到极致。高粱颗粒,磨成面粉前先用水煮,晾干磨面过罗时,分成“头罗面”“二罗面”乃至粗粝不堪的“三罗面”。待客时,挖两碗精细的“头罗面”,放在面盆搁开水锅里蒸腾,有了这个环节,搓成的“鱼鱼”才顺滑可口。如果配菜是猪肉蒜薹炒粉条,在“老忻州”看来简直就是人间至味。现在一说“豆腐脑儿”,店家就强调“铜锅”,似乎忻州“豆腐脑儿”是因为“铜锅”才好喝。其实,老忻州的“豆腐脑儿”与别处不同,除了细嫩至极、舀起来颤颤巍巍的老豆腐,还有细粉丝和勾芡上色的汤汁。不要小瞧这看上去黑红黑红的汤汁,所上之“色”须用白糖熬成。要是倒上一股“老抽”,颜色倒是有了,味道、口感乃至神韵便一概皆无。
“茭的鱼儿”。摄影张媛
物产贫乏,逼迫“老忻州”“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。
当年忻县油料植物种植很少。计划经济年代,即便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也仅可凭证购三两植物油,炒菜、调凉菜只能点点滴滴。红白事宴过大年,席面上少不了油糕。忻州“西八县”油料多,困难年代百姓也是油炸糕。“老忻州”把蒸好的糕包少许红糖,放在滴了几点胡油的鏊子上,油温起来后把糕在鏊子上使劲儿擦来擦去,恨不能把胡油的分子也擦在糕上。老忻州的“擦糕”两面金黄,倒也软糯香甜。只是,一个“擦”字,折射出当年百姓多少无奈和心酸。
瓦酥也是老忻州特产。一种食品,何以跟建筑材料搭上关系?传说早年忻州某村一个财主想吃顿好的(注意,还是财主),但搜寻一番家里只有几颗鸡蛋、半升白面和瓶底子上的一点儿胡油。这“吃货”老财不肯罢休,打鸡蛋、倒胡油和了一小团面,可是家里又没有烙饼的鏊子。情急之下,将面团抻开搁在瓦楞上举火烤之。烤熟后吃在嘴里,居然稣香绵沙,入口即化。这种像瓦片的烘烤食品,因此得名“瓦酥”。后来,做“炉食”的师傅们加以改良,瓦酥才成为老忻州的一大特色。庚子年八月十五西太后西逃路经忻州,当地官员奉上此物,慈禧品尝后赞不绝口,还赐名“龙凤瓦酥”。现在制作瓦酥,选用精粉、纯蛋黄、上等食油、细砂糖,成形时用模托就,油炸出锅后压制成瓦状。外地人逛忻州古城,总要带走一斤二斤。
瓦酥
老忻州的特产,还有“忻州养胃糕”。在“养胃糕”前冠以“忻州”,足见此物为忻州独有或忻州出品的最为地道。其制作方法,几个版本的《忻州志》中均有记载:“江米过筛,磨为细粉。先上笼蒸,再入炉烤。”“忻州养胃糕”色呈浅黄、甜酥可口,在“老忻州”看来食疗两宜,胃口不好的老者常吃有益。
麻会,是忻府区的一个古村落。“麻会糖枣”,也是老忻州的一种特色食品。现在的做法,是将饴糖、色拉油用开水冲开,加入面粉中拌匀打成面穗,将面穗与红糖调成的糖油汁混合成面团,将面团搓成长条切成方形剂子,入油锅炸成黄红色。捞出倒在盆里,在其表面裹一层蒸熟过筛的面粉和绵白糖。做好的“麻会糖枣”其状若枣,外表棕褐,里面芯黄,口感酥甜软绵。
麻会糖枣
瓦酥、养胃糕、糖枣,同干馍馍一样,都是“老忻州”开发的极具忻州地方特色的“搬着”吃的食品,把它们理解成“点心”也没有问题。这些吃食,就是“老忻州”永远的乡愁。
3
溯 源
李文虎的爷爷李有年,大约是20世纪的同龄人。14岁那年,李有年跟忻州城东西两街、南北两关的众多贫民家庭的子弟一样,到城内财东所开的字号当学徒,学会了打干馍馍的手艺。
民国10年至民国19年,被认为是忻县商业的黄金时期。不说走口外的忻县商人,其时忻县城内就有工商户400余家,南北大街、东大街、南北两关店铺林立,几大行业的字号货物齐全,种类繁多。1935年,忻县全县20万人口,从商者竟将近4万。五六人中有一人经商,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。在众多商家中,那些资本雄厚、经营有方、货真价实的字号成为百姓购物的首选。当时流传一句“顺口溜”:“要买绸缎穿,公益昌、聚德昌;要吃好点心,文盛楼、德盛楼、兴盛楼、桂香楼;要下好馆子,庆升园、万和园、同和园、会林园。”
文虎说,他爷爷当年学徒的店铺,是东楼村张姓财东所开的字号“聚德昌”,地址就在后来南北大街上的“职工俱乐部”。不过,从上述“顺口溜”看,“聚德昌”应该是家绸缎庄。或许是李有年给孙子讲故事的时候年老健忘,或许是因为财东当时开的买卖太多而张冠李戴?不得而知。
李文虎祖父李有年(左)
检索资料,发现李有年学徒的店铺可能是“聚义德”——也是东楼村张姓财东开的买卖,这是一家百货店,符合李文虎回忆其祖父“店里甚也有,干馍馍只是个捎带”的描述。
清末民初,忻县生意人中有“七大富商”之说,其中双堡村的郜家、樊野村的王家、东楼村的张家又为其中的翘楚。李有年所说的张姓财东,应该是指东楼村的张洪钧及其子官文、仁文——从光绪到清末民初,华北五省“聚”字打头商号的财东都是张氏父子。各商号每年的收入以白银计,总数在三万两以上。
现在看来,当年忻县的大买卖人做生意还真是细大不捐,既拣西瓜也不丢芝麻,只要顾客有需求,就统统在经营之列。李文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打干馍馍时,每个售价6毛钱。民国初年一个干馍馍售价几何无从考证,想来顶多一两个铜子儿。
李有年学成手艺后一直服务东家,直到解放后“公私合营”,店铺归入忻县饮食服务公司,李有年成了挣工资的工人,依旧打干馍馍。退休后,在自家小院悄悄垒起泥火炉,每天打几十个出售补贴家用。按理说当时不允许个人经营,只是这打干馍馍的买卖实在太小,没准儿“执法人员”也好这一口,就对李大爷睁一眼闭一眼。
文虎的父亲李黄根生于1938年,至今健在。李黄根少年时跟父亲学会打干馍馍。打了几年实在不挣钱,不得不改行学了木匠。文虎初中毕业后,跟父亲“走东家”打家具、起房盖屋,虽说挣不了什么大钱,倒也不误盖房娶媳妇。如果不是行业发生了变化,他也未必继承祖业。
李文虎与父亲李黄根
90年代前后,人们盖房再不是土木结构,都盖钢筋混凝土的“现浇房”,木制门窗也逐渐被铝合金门窗取代,“老木匠”们一下变得再无用武之地。李文虎也想过改行,但不论是囿于“人过三十不学艺”,还是缺少必要的资本,总归是“赋闲”在家。有一天收拾小南房,看到旮旯里蒙尘已久、爷爷留下的泥炉子、铁鏊子和干馍馍锤,想想父亲经常对他说的“走一处不如守一处”,这才重新支起了李家打干馍馍的摊子。
这一打,就是小三十年。
4
炉具、炉火的变迁
“老忻州”把各种饼子、糕点统称“炉食”——用炉火烘烤的食物。李文虎打干馍馍的摊子,算是最小的“炉食铺”。
李有年打了几十年干馍馍,一直用泥炉子,炉中所烧只用湿“煤糕”。李黄根也用泥炉打了几年,后来便做了木匠。李文虎支摊子的时候,有了更趁手的工具——蜂窝煤炉。七八年前,因为环保的原因蜂窝煤炉不能使用,遂改用罐装气的天然气灶,上置铁鏊烘烤。文虎说,现在忻州打干馍馍的,除他之外都用烤箱。烤箱加工的量大,但口感、味道总归逊色于用鏊子烘烤。
百年前的炉鏊
当年为什么用煤糕还得是湿煤糕?这是因为干馍馍除了一个个上鏊时须用急火令其在鏊子上“执”(立住、成型)住,这个时间不到一分钟,剩下的半个小时只能用文火,且火苗不能直及鏊底,须用一个叫“遮火”的物件将火焰盖住。干馍馍在炉鏊中其实不是被火烤熟的,而是生生被炉温烘熟。惟其如此,生干馍馍中的水分才能被慢慢“逼”干,口感是脆的。不似烤箱烤出的,虽然“干”则干矣,但难免硬得咯牙。煤糕中一少半是“胶泥”土,燃烧值自然不高。加之又是湿的,自然符合“文火”的要求。而老忻州另一种类似食品“斜尖子”则与烘干馍馍相反,上炉鏊后要用急火一气呵成。
现在的年轻人,早已不知“煤糕”为何物。可忻州人中“60后”往上的,谁小时候没有打过煤糕?
山西是“煤海”,按理说不缺煤烧。但在计划经济时代,冬天生炉子取暖的块儿炭不好买,百姓即使能买到也买不起,只好买回便宜的面儿煤,再掺上不要钱的胶泥土打成长方形的“煤糕”。“煤糕”中煤与土的比例大约是2:1或3:2,因此“老忻州”也把“煤糕”叫作“泥糕”。
每年国庆前后,家家户户集中打“煤糕”。此时雨水已少而气温尚高,方便“煤糕”晾晒。忻州人当年打煤糕,胶泥土都是从西街、南街的土崖上刨得。老辈儿说,这土崖其实就是城墙的夯土堆。用??头把夯土砍削下来,其截面可见白色的细纹。煤面过筛,胶泥土拍碎,按比例混合堆成小丘。从小丘顶端扒坑,渐次扩大,坑中倒水后从小丘底部铲煤土掩埋。“闷”个把小时后,将煤土与水充分搅拌呈泥状,铲一锹倒入木制或铁制的模具。用忻州人所说的“腻页”也就是小铲把煤泥摊平、中间略鼓、四角压实、表面抹光。起模,待晾晒至半干时将其搬起侧立加速风干,干透后摞起码放在窗台底下。泥糕子是块儿炭的代用品,一冬天生炉子取暖、烧水就指着它了。
当年打“煤糕”。图片源自“太原道”公众号
“煤糕”。图片源自“太原道”公众号
李有年打干馍馍时,泥火炉砌在当地,挨着揉捏、敲碾干馍馍的面案。泥炉子没烟囱,烧的又是湿煤糕,烟气氤氲弥漫,把李大爷呛成了气管炎,到了冬天就得吃药输液。李文虎一开始就把摊子支在自家门洞,烧蜂窝煤基本无烟,空气流动,二氧化碳也不甚呛人。用上天然气灶后,屋内打制,室外烘焙。只是,一个月用四罐气,一罐一百多,无形中加大了干馍馍的成本。
5
悠然笃定的手艺人
为了打好每天这百十个干馍馍,李文虎上午、下午没有一点儿歇空。
文虎打干馍馍,从和面到出炉全部手工。现在加工面食食品的都用和面机,省时省力。文虎不用和面机,认为手工和面才能随时感知面的软硬,反复揉搓,直至达到理想状态。上、下午各8斤白面和好后,往盆中倒斤半胡油,加三斤面粉,搅拌油、面,令其成为像糁子一样的“酥”。将酥与和好的面反复搅揉,并不时加入少许干面粉,最后揉成一个发黄的大面团。
忻州所有打干馍馍的师傅中,只有李文虎在和面时“加酥”。看外观,别家的干馍馍黑白分明,只有李家的色呈褐黄。加酥时加干面粉也是李家的独到之处,文虎说,不加面粉,干馍馍吃起来就没有那个“脆”劲儿。
加酥
“高手在民间”系列有一篇《“邢家老号”黄烧饼》。定襄县城打黄烧饼最有名的“二门市”的邢快生师傅,做黄烧饼时也要加酥——用白砂糖、精面粉、胡麻油按5:5:3的比例制成酥料,把皮面压成薄饼状后将酥料包起,擀成长方形的厚面片,将面片卷起,揪成面剂子。无论李师傅还是邢师傅,做“炉食”时加酥的目的,都是为了食品在常温下放个十天半月后,吃起来依然酥香如初。
做黄烧饼时加酥
定襄“邢氏黄烧饼”
文虎把一大团面分成七八个小面团,每个面团揪成八个面剂子。每揪一个,迅速用湿笼布遮上。依次拿出面剂子,双手反复揉捏,捏成中间略薄、周边较厚的面饼。小勺挖一克左右的盐倒在面饼中间,四周围拢,将面饼揉捏成桃状,再用湿笼布遮盖——这也是面剂子进一步饧发、柔和的过程。
干馍馍锤是手打干馍馍的惟一工具。锤头由老杏木刻削而成,鸡蛋大小。这柄小锤,李有年当年学徒时师傅留给他,至今已逾百年。油迹深入木质肌理,油光可鉴,发出暗红的光泽。手柄几年前用坏,文虎重配了一个。
文虎取出包好盐的桃状面剂,左手护持,右手执锤由内而外锤碾,动作潇洒至极。干馍馍有正反面,先揉捏反面也就是中间“钵儿”大者,锤碾手围、拧挤按压。反面成形后,翻过来正面也照此办理。揉捏、锤碾一个,用时约摸两分钟。做完一个又来一个,动作没有丝毫停顿。文虎说,不管正面、反面如何锤碾,必须保证包进面剂中的那一点儿盐永远处在中心位置,也就是烤好后的膨起部位。没有这一点盐,干馍馍吃起来难免寡淡——这点儿盐,就是干馍馍的灵魂。
锤碾
上鏊,先用急火令干馍馍的正面“执住”,此过程不过半分钟。移鏊离灶,在灶眼上放铁焊的“遮火”,“遮火”上再放个铁盖子,保证鏊底不见明火。干馍馍的正反面各烘焙约15分钟,这个空当,文虎回屋揉捏、锤碾下一鏊的八个。如此循环往复,一上午烘焙七八鏊、总计五六十个干馍馍。
上鏊
文虎说,打干馍馍关键是掌握火候。鏊盖揭早了干馍馍粘牙,揭晚了自然会烤焦。出鏊后必须晾凉,否则装袋后容易返潮。天冷时好说,夏天出鏊后要用风扇吹凉。待完全冷却后,要用刀一个个削去正反面凸起部位的焦黑。和面、加酥、揉捏、加盐、锤碾、上鏊、烘烤、晾凉、切削,经过这一套环环相扣的工序,一个售价两块钱的干馍馍才算完成。
切削
上门买干馍馍的,基本都是老主顾。有的顾客见文虎这般辛苦也给他“支招”:别家用和面机和面还不加酥,加工也用上了机器,出来基本上就是成品,用烤箱一天能打几百个,你咋就这么死心眼儿?文虎笑笑:这样做出来口感、口味变了,你还会“照顾”我?
“李氏干馍馍”除了忻州人买,呼市、包头、丰镇当年“走西口”“上北路”的忻州人的后代中,小时候回忻州吃过他李家干馍馍的,几十年过去仍念念不忘。一年冬天,劳累一天的文虎已经睡下,听得有人“哐哐”砸门。开门一看,一位老主顾先忙不迭地道歉,接着说在包头的年过九旬的舅舅生命垂危,已是弥留状态。表兄打来电话说,老人嘴里念叨了几遍“干馍馍”,因此拜托表弟带上“最正宗的忻州干馍馍”连夜动身赴包头,了却老人最后的心愿。白天打下的一个不剩,文虎赶紧和面、揉捏,紧赶慢赶打出一鏊。几天后,老主顾带着表兄表妹给拿的礼品登门致谢,说老人吃了一口后,终于心无挂碍,安详西去。
从一头黑发打到两鬓斑白,李文虎恪守爷爷留下的“生意虽小,招牌事大”的信条,几十年来打干馍馍的工本、程序毫不走样儿。收入仅能温饱,却也怡然自得。
当下,无论做什么都追求一个“快”字。李文虎不受其扰,悠然而笃定。他虽然挣不到几个钱,日子却也照样过得安稳自在。
作者:郭剑峰 冯晓磊 赵菁
来源:忻州在线